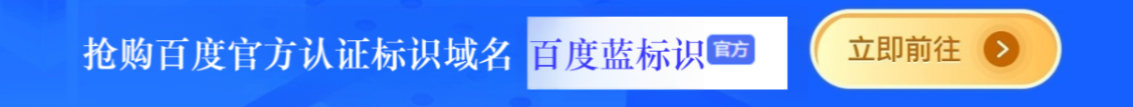在2021年,西北地区的校园戏剧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主要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法,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单一途径实现“现代化”的演绎。
一、单一的“被现代化”
女性现代化的路径问题长期占据学术讨论的核心位置。部分学者提出,女性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常常是在文化及知识上较为成熟的男性引领下进行的。在这种视角中,女性往往被置于“被解放”的境地,她们在相当程度上被男性看作是“玩偶”,因而始终未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某些观点提出,关于女性解放的探讨,实则暗示了女性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将她们视为有待被解放的客体。这种看法并非孤立存在,即便是鲁迅在《伤逝》中所塑造的女主角子君,她的追求女性解放的过程,亦是完全依赖于男主角涓生的启迪。
然而,我坚信女性意识的觉醒并非只有一条途径。在我看来,女性的觉醒更体现为一个丰富多彩的过程。张红萍曾言,“妇女的解放虽受先进人士的提倡与引领,但真正的变革动力源自女性自身。”她明确指出,解放并非仅是男性主导的事务,女性同样在变革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的觉醒主要源于内心的驱动力,而非外界的影响。
在西北地区的红色校园戏剧里,女性角色的觉悟往往源自男性的启迪。以西北民族大学满天星剧团的《映山红》为例,剧中的梁玉梅、潘慧珍以及陈兰英,她们均是在丈夫——一位共产党员的感召下,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比如咸阳师院剧社的《国茯》中,崔再冰在丈夫对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继续传承了丈夫的思想。李薇在西安音乐学院实验剧团的《战火青春》中扮演的角色,她前往延安的决心源于对暗恋对象的崇拜,但随后该领导背叛,这使得李薇开始意识到必须独立思考,真正觉醒。
西北政法大学南山剧社的《庄严的审判》里扮演刘茜的角色,她的信仰来源尚不明确,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与她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有关。尽管这些作品里展现了男性引导女性觉醒的故事情节,这样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这种模式在创作中频繁出现,就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思考。从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创作模式反映了男性主导的思想倾向。尽管这些作品受到了女性主义的深刻影响,然而,女性角色在作品中的真正自主性以及思想上的独立自主性,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男性主导的束缚。
二、过于结构化的叙事套路
西北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校园戏剧,无论是《国茯》中那充满复仇色彩的情节,还是《映山红》里讲述拯救的故事,抑或是《战火青春》中描绘的冒险之旅,都显现出一种模式化的剧情布局。即便《国茯》与《战火青春》采用了双线叙事手法,它们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布局仍未能跳出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阐述的七种典型角色类型:英雄、对手、冒牌英雄、目标及其拥有者、派遣者、赠予者以及协助者。特别是《战火青春》,其角色定位极具代表性:李薇扮演英雄角色,叛逃者充当伪英雄,延安成为目标,国民党扮演反派角色,小胖子则扮演赠予者,红军则成为协助者。这部音乐剧的叙事框架颇似一部公路片,其中角色塑造与故事情节均充斥着典型的模式化元素。
《国茯》亦未能幸免于这一模式,剧情从高队长说服穆建堂投向国民党,到崔再冰登场揭示矛盾,其发展走向几乎一目了然。尽管高队长这一角色相较于其他角色更为丰满,但总体来看,剧情与人物的设定几乎都在观众的预期之内。

这种模式化的叙述手法,尽管对作者的创作有所助益,却也让观众对故事走向有了先入为主的预判,进而难以激发更深的情感共鸣。倘若作者不能打破这种既定思维,角色塑造将显得单薄无力,观众亦难以与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际上,此类作品多属于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实用主义”理论范畴,其创作宗旨在于激发观众的情感并实施教化。然而,这种模式化的剧本架构却变成了阻挡观众情感共感的障碍,与创作的初衷渐行渐远。
因此,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需特别关注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一方面要保证故事叙述的连贯性,另一方面还需勇于创新表现形式,以打破观众的预期和固有思维模式,提升故事的吸引力,并赋予角色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注释:
王宇在其文章《现代性与被叙述的“乡村女性”》中,对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5期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页码范围是85至91。
宋剑华在其著作中探讨了“玩偶”这一形象,指出其被赋予了“娜拉”的象征意义,并认为这是一个启蒙时代所塑造的虚构神话。该文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页码为102至111。
高雁在《名作欣赏》2017年第32期发表的文章中,探讨了“从庭院到广场——现代中国女性的解放道路”,该文编号为39-43页。
张红萍在其文章中,对“妇女是被解放的”这一话语进行了深入剖析,探讨了百年间妇女自我解放的历程。该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1期,页码为89至113。
(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所著的《故事形态学》一书,由贾放翻译,于200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